帶臺灣到南極,與星空相會
帶臺灣到南極,與星空相會:專訪陳丕燊教授(首次發表於2012.1)
能成功攻頂喜馬拉雅山聖母峰功頂,必定是位身強力健的年輕登山運動家;但是,創下海拔3千多公尺南極極頂登頂的台灣第一人、恐怕也是華人學界的第一人,卻是已過天命之年、文質彬彬、充滿智慧的台大物理系教授;他為台灣的天文物理學界在國際舞台上爭得重要的地位。
【錄影訪談】校史館張安明、陳南秀
【文稿撰寫】校史館陳南秀
建國一百年的歲末,校史館接到學術副校長羅清華的電話,希望校史館能徵詢參與天壇陣列的陳丕燊教授同意,將陳教授親手繪製曾在南極飄揚的中華民國國旗,讓校史館收藏並展示。非常感謝羅副校長的提醒,校「史」館雖然以保存臺大過去的歷史為主,但這面國旗記錄著民國一百年來,臺灣首次參與南極國際級科學實驗的重要里程碑,別具歷史意義,於是校史館獲得了親訪陳丕燊教授的機會。


採訪當天在陳丕燊教授辦公室的一隅,我們親見了曾在南極極頂飄揚的手繪國旗。這面國旗是陳教授耗費十幾個小時,在南極唯一的美術工作坊中,運用麥克筆和壓克力顏料,一筆一劃親手繪製而成的。
由於陳教授抵達南極是在建國百年,以及人類登上南極的一百周年,所以他心生一計,在正反面的白日中,分別畫上了藍色與紅色的數字100,記錄著這「雙百巧合」。
「天壇陣列」觀測台,在南極極頂占地一百平方公里,由三十七座天線站組成,藉由觀測南極冰層中的宇宙微中子來探究宇宙邊緣所發生的事情。臺大梁次震宇宙學與天文粒子物理研究中心的陳丕燊教授,即是主導此科學實驗的一員,在國際天文物理學界已有高知名度的陳教授,用淺顯易懂的語言為我們解釋什麼是宇宙微中子,又為什麼要選在南極做實驗、以及在南極架設第一座天線站的辛苦歷程。(詳細過程,稍晚請參見臺大校史館口述歷史)
學生時代磨製的八吋望遠鏡
陳教授在分享天壇陣列的過程時,一再強調他今日之所以能登上南極,成為主導這次實驗的一員,要非常感謝梁次震宇宙學中心,提供他能在國際上發揮的平台。梁次震先生為了促成他離開已工作多年的史丹福大學回國服務,四年前慷慨地捐贈兩億元給臺大,成立了這座研究中心。
梁次震與陳丕燊教授是臺大物理系的同學,回想當年,他們這一群對物理具有高度熱誠的學子,在丘宏義教授的指導與鼓勵下,由同班同學葉炳輝帶領,曾經一同利用課餘的晚間,輪流至物理系館二樓崔伯銓教授的光學實驗室,土法煉鋼地磨製八吋望遠鏡。所用的鏡片是他們從基隆市的廢船拆解中心低價收購來的,就這樣鐵杵磨成繡花針,全臺第一架的八吋望遠鏡因此而誕生了。
當時只是幾位物理系同好課餘閒暇投入在天文學的探索,並沒有向校方申請成立學生社團;後來台大學弟妹成立了「天文社」,聽說有時他們會「禮貌性」地將社史源頭追溯至這群物理系老骨頭在二號館屋頂、平台觀測星象的草鞋時期。
雖然當年大家同心協力磨製的八吋望遠鏡現在已不知去向,但是他們同窗的情誼依然延續至今,「我覺得非常湊巧,梁次震和我攜手,由我打前鋒,他出錢,來了解宇宙最深的地方,就像我們當年一起磨望遠鏡鏡片,精神是完全一樣的。」而且他認為天壇陣列是更擴大化,替臺灣在國際上發光。
在我頭上者,群星之天空
另外,我們詢問教授一幅當年學生時代的畫作,讓他憶起一九六八年十九歲那一次的感動,原來對宇宙智慧的想望,一直深深根植在他內心深處。
陳教授在臺大物理系就讀時,喜歡在舊總圖遼闊的大廳讀書。大一新鮮人的他,有次坐在閱覽桌前,抬頭向上望,一個富有想像力的念頭突然閃過腦海:「如果現在頭上沒有天花板,這個星空將是多麼希臘。星光下,智慧真的是和宇宙相連。」這彷彿是余光中〈重上大度山〉詩句裡的畫面:「星空,非常希臘」。余光中正是陳丕燊喜愛的詩人。
當下,他立刻在紙上隨便勾勒幾筆,就騎著腳踏車直奔回家,花了一個晚上,把這幅「在我頭上者,群星之天空」的舊總圖畫作完成。由於陳教授非喜歡哲學,從中學時期就開始大量閱讀了許多哲學書籍,尤其景仰康德哲學。因此這幅畫作也充滿了「在我頭上者,群星之天空」的康德意象。這句話出自康德的墓誌銘,下一句是「在我心中者,道德之法則」,陳教授對這兩句話的境界非常心嚮往之。
探究物質的基本結構原理,也就是所謂的基本粒子,是最讓物理學子感到興奮的。所以他出國留學讀的就是基本粒子物理,但他萬萬沒有料到,到了九〇年代,天文學和宇宙學進入了一個文藝復興時代,讓他了解到知識是能夠推到宇宙剛誕生的時候,宇宙誕生是極高能、極高密度、極高溫爆發出來的大霹靂。二十年以來,宇宙學和粒子物理學結合成一體,所以想要了解宇宙學,就不得不了解基本物理,反過來亦如此。
當年「在我頭上者,群星之天空」,現在陳教授回頭看,好像是一個預告,將來有朝一日他要再跟宇宙學相聯繫。

訪談中陳教授笑言心中最理想的圖書館閱覽廳是一處沒有屋頂、可以直接呼吸宇宙能量的閱讀空間。我們問,下雨怎麼辦?他說,就臨時伸展玻璃罩擋雨就好了呀!

陳教授從小就有繪畫、音樂的天分,訪談間陳教授展示他家人挑選他過去的畫作,製作而成的年曆,並開心地為我們解說每幅畫是在何時何地,又如何繪成的。
訪問到了尾聲,我們已經收起了錄影機,依舊與教授繼續聊著方才的種種話題,陳教授突然感性地說:隨著年歲漸長、也能如願以教授及研究物理做為終身的職志,但是現在回首十九歲的那幅 ‘星空就在頭頂看顧著我成長’ 的畫作,對早年的那個初生之犢、胸懷宇宙的少年陳丕燊不免心生感動:那位少年是如此的「真」,願望是如此的「無窮大」;而,天壇陣列發起人的「我」,距離實踐「他」當年所擁抱的那份純真又遠大的夢想,依然是如此遙遠的無窮大...
【校史館/張安明/首次發表於2012.1】
能成功攻頂喜馬拉雅山聖母峰功頂,必定是位身強力健的年輕登山運動家;但是,創下海拔3千多公尺南極極頂登頂的台灣第一人、恐怕也是華人學界的第一人,卻是已過天命之年、文質彬彬、充滿智慧的台大物理系教授;他為台灣的天文物理學界在國際舞台上爭得重要的地位。
【錄影訪談】校史館張安明、陳南秀
【文稿撰寫】校史館陳南秀
建國一百年的歲末,校史館接到學術副校長羅清華的電話,希望校史館能徵詢參與天壇陣列的陳丕燊教授同意,將陳教授親手繪製曾在南極飄揚的中華民國國旗,讓校史館收藏並展示。非常感謝羅副校長的提醒,校「史」館雖然以保存臺大過去的歷史為主,但這面國旗記錄著民國一百年來,臺灣首次參與南極國際級科學實驗的重要里程碑,別具歷史意義,於是校史館獲得了親訪陳丕燊教授的機會。


採訪當天在陳丕燊教授辦公室的一隅,我們親見了曾在南極極頂飄揚的手繪國旗。這面國旗是陳教授耗費十幾個小時,在南極唯一的美術工作坊中,運用麥克筆和壓克力顏料,一筆一劃親手繪製而成的。
由於陳教授抵達南極是在建國百年,以及人類登上南極的一百周年,所以他心生一計,在正反面的白日中,分別畫上了藍色與紅色的數字100,記錄著這「雙百巧合」。
「天壇陣列」觀測台,在南極極頂占地一百平方公里,由三十七座天線站組成,藉由觀測南極冰層中的宇宙微中子來探究宇宙邊緣所發生的事情。臺大梁次震宇宙學與天文粒子物理研究中心的陳丕燊教授,即是主導此科學實驗的一員,在國際天文物理學界已有高知名度的陳教授,用淺顯易懂的語言為我們解釋什麼是宇宙微中子,又為什麼要選在南極做實驗、以及在南極架設第一座天線站的辛苦歷程。(詳細過程,稍晚請參見臺大校史館口述歷史)
學生時代磨製的八吋望遠鏡
陳教授在分享天壇陣列的過程時,一再強調他今日之所以能登上南極,成為主導這次實驗的一員,要非常感謝梁次震宇宙學中心,提供他能在國際上發揮的平台。梁次震先生為了促成他離開已工作多年的史丹福大學回國服務,四年前慷慨地捐贈兩億元給臺大,成立了這座研究中心。
梁次震與陳丕燊教授是臺大物理系的同學,回想當年,他們這一群對物理具有高度熱誠的學子,在丘宏義教授的指導與鼓勵下,由同班同學葉炳輝帶領,曾經一同利用課餘的晚間,輪流至物理系館二樓崔伯銓教授的光學實驗室,土法煉鋼地磨製八吋望遠鏡。所用的鏡片是他們從基隆市的廢船拆解中心低價收購來的,就這樣鐵杵磨成繡花針,全臺第一架的八吋望遠鏡因此而誕生了。
當時只是幾位物理系同好課餘閒暇投入在天文學的探索,並沒有向校方申請成立學生社團;後來台大學弟妹成立了「天文社」,聽說有時他們會「禮貌性」地將社史源頭追溯至這群物理系老骨頭在二號館屋頂、平台觀測星象的草鞋時期。
雖然當年大家同心協力磨製的八吋望遠鏡現在已不知去向,但是他們同窗的情誼依然延續至今,「我覺得非常湊巧,梁次震和我攜手,由我打前鋒,他出錢,來了解宇宙最深的地方,就像我們當年一起磨望遠鏡鏡片,精神是完全一樣的。」而且他認為天壇陣列是更擴大化,替臺灣在國際上發光。
在我頭上者,群星之天空
另外,我們詢問教授一幅當年學生時代的畫作,讓他憶起一九六八年十九歲那一次的感動,原來對宇宙智慧的想望,一直深深根植在他內心深處。
陳教授在臺大物理系就讀時,喜歡在舊總圖遼闊的大廳讀書。大一新鮮人的他,有次坐在閱覽桌前,抬頭向上望,一個富有想像力的念頭突然閃過腦海:「如果現在頭上沒有天花板,這個星空將是多麼希臘。星光下,智慧真的是和宇宙相連。」這彷彿是余光中〈重上大度山〉詩句裡的畫面:「星空,非常希臘」。余光中正是陳丕燊喜愛的詩人。
當下,他立刻在紙上隨便勾勒幾筆,就騎著腳踏車直奔回家,花了一個晚上,把這幅「在我頭上者,群星之天空」的舊總圖畫作完成。由於陳教授非喜歡哲學,從中學時期就開始大量閱讀了許多哲學書籍,尤其景仰康德哲學。因此這幅畫作也充滿了「在我頭上者,群星之天空」的康德意象。這句話出自康德的墓誌銘,下一句是「在我心中者,道德之法則」,陳教授對這兩句話的境界非常心嚮往之。
探究物質的基本結構原理,也就是所謂的基本粒子,是最讓物理學子感到興奮的。所以他出國留學讀的就是基本粒子物理,但他萬萬沒有料到,到了九〇年代,天文學和宇宙學進入了一個文藝復興時代,讓他了解到知識是能夠推到宇宙剛誕生的時候,宇宙誕生是極高能、極高密度、極高溫爆發出來的大霹靂。二十年以來,宇宙學和粒子物理學結合成一體,所以想要了解宇宙學,就不得不了解基本物理,反過來亦如此。
當年「在我頭上者,群星之天空」,現在陳教授回頭看,好像是一個預告,將來有朝一日他要再跟宇宙學相聯繫。

訪談中陳教授笑言心中最理想的圖書館閱覽廳是一處沒有屋頂、可以直接呼吸宇宙能量的閱讀空間。我們問,下雨怎麼辦?他說,就臨時伸展玻璃罩擋雨就好了呀!

陳教授從小就有繪畫、音樂的天分,訪談間陳教授展示他家人挑選他過去的畫作,製作而成的年曆,並開心地為我們解說每幅畫是在何時何地,又如何繪成的。
訪問到了尾聲,我們已經收起了錄影機,依舊與教授繼續聊著方才的種種話題,陳教授突然感性地說:隨著年歲漸長、也能如願以教授及研究物理做為終身的職志,但是現在回首十九歲的那幅 ‘星空就在頭頂看顧著我成長’ 的畫作,對早年的那個初生之犢、胸懷宇宙的少年陳丕燊不免心生感動:那位少年是如此的「真」,願望是如此的「無窮大」;而,天壇陣列發起人的「我」,距離實踐「他」當年所擁抱的那份純真又遠大的夢想,依然是如此遙遠的無窮大...
【校史館/張安明/首次發表於2012.1】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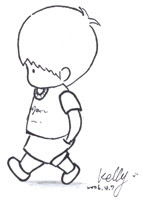
留言
張貼留言